執行成果
分項計畫1: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所務建置
{{ $t('FEZ002') }}人文學院|
計畫名稱:11G205-7高教深耕人文學院基本款
計畫分項: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所務建置
具體措施:文學所創作發表暨合作出版計畫
執行單位:人文學院
印刻文學生活誌2022年8月號228期,封面專輯「種詩的人 吳晟」,刊登本所學生蕭宇翔文章〈萬物自然生長〉。
文中所述背景起源於一次邀約,幾位年輕詩人至吳晟老師家換宿,因而留下關於土地,也關於生活、關於詩的記憶。〈萬物自然生長〉以吳晟詩句「日日,從日出到日落」為引,在「黃昏」、「日出」、「日落」、「人定」四個段落中,講述田園,亦寄寓創作者於天地之間,為萬物包圍的思索與感悟。
▍以下全文
〈萬物自然生長〉
❝ 日日,從日出到日落──吳晟〈泥土〉❞
◇黃昏
面前是一條長而漆黑的森林隧道,水圳的支流在一旁轟隆作響,成排的樟樹和毛柿簇擁著盡頭,微微的光源,指引我和幾名同伴,持手電筒,試探腳下的碎石,並看見不遠處飄游的螢火蟲。朗月下,我們正從樹林深處的小屋,步出純園,前往隔壁田區裡一座三合院,吳晟老師的家。
對於夜晚的純園來說,我只是借宿的過客,真正的主人應該是這些台灣窗螢,牠們的幼蟲正在茂盛的落葉裡攢動,以鐮狀大顎鉗住蝸牛,以尖針注入激越的消化液,無聲地吸食著肉糜。明天一早,我將撿到一具具空洞的蝸殼。
而成蟲們此刻在空中熒熒交換著光熱,這是牠們最為熟練的旗語──源於一股獨立而自持的神經衝動,起念之際便迅速傳送到發光細胞,磷,就在氧化中釋出能量──冷冷的光。這種語言在訴說些什麼?求偶,警示,溝通,有時候,牠們也欺騙。母妖掃螢就會模仿異族母螢火蟲的回應訊號,吸引那些疲於奔命但一無所獲的公螢火蟲,然後把牠們抓起來吃掉。
這在其他昆蟲身上也屢見不鮮。流星錘蜘蛛常模擬雌蛾散發的性費洛蒙氣息,吸引雄蛾到牠嘴邊的溫床上就頸。而現代農業已能利用性費洛蒙集中害蟲,加以捕殺,摧毀牠們一整季的繁殖計畫。
語言,這星球上所有物種的任何語言,似乎都難逃「造假性」,絕非人類的專利而已。這對寫作者而言有時候是福音,代表我能在想像中戮力捏塑一種通脫而恰韻的理想型,但更多時候,我感到困苦不已。
隧道將盡時回頭一望,螢蟲的光亮已逸散在深處。我們手中光筒,唇邊細語,走動時氣流,已對牠們造成嚴重打擊。在過季時分,廣闊的林田上牠們飄忽不定,野外的壽命只有三到七天,白日食露水,到了晚夜則奔波於繁殖的使命,不察時間的流逝,而時間即生命。我突然感到牠們和我一樣徬徨,享用著天賜的妙能與異稟,卻不知一己微軀究竟身處何地。
◇日出
這天上午,一隻鶇科在頭頂,上層的樹枝間覓食,跳躍,感覺我的一舉一動,我高舉的鋤頭,正往純園裡的雜草揮去。
牠有著暗黃的尖嘴,橙紅的胸羽,絕對的專注與機警,很後來我才認出那是一隻赤腹鶇,因我在漫長的勞動下試著放空,投入這全身心的運動,彷彿一種瑜珈,將荒廢日久的肉身喚醒。相比之下,思維,情感,語言這些都不是生命的本來面目,只是些可有可無的枝葉,不如說,雜草。有時是根淺而有毒的姑婆芋,大多時候是放肆的咸豐草與蔓澤蘭。這個園子裡還有抓地不放的構樹,拔心不死的陰香。而有著橘黃色漿果,晶瑩剔透的瑪瑙珠,它本是一種觀賞用的外來種,和我的眾多思想一樣,外表玲瓏可愛,內裡嬌慣兇悍,還帶著雖然不痛不癢的小毒。
但月桃葉可以剪下來包裹食物,桑葚葉可以煮一鍋消暑的茶,烏心石的殘枝可以鋸為手杖。這些都是在純園務農時,吳老師的妻子,莊老師告訴我的。這就是我來純園的第一個體悟:讓最喑啞,淡漠,低微的聲音來告訴我,我的心該怎麼做。這些在世上被目為解析度最低的佈景,陪襯,消耗品,不精緻,不起眼,若非我一時的好奇,將立時消失於揚起的土塵。就像在我奮力鋤動樹下雜草時,土穴裡飛滾的小甲蟲,截成兩半的蚯蚓,閃閃發亮但再也不動的金龜子與蟬。這些鮮豔的臉譜,牠們都曾為生命而努力。
在剷除這些草木前,我得先學會辨識它們。然而辨識它們後我開始疑惑,到底什麼是雜草?一名夥伴在揮鋤時問我:姑婆芋不好嗎?我答不出。
如果我用的是天地,而非以人類的尺碼來度量──或許人類與雜草也沒有什麼分別,同樣是混亂無章地生長著,恣意而自然地出生,毀滅,出生,如此反覆,彷彿原始植披的遷徙史,遍染所有陸塊,即使最極端的氣候也不例外。以天地的尺碼來度量,則所有的生物,在與地球系統的相互作用下,自有它如樂曲般有機發展,自動協調,自我圓融的整體。況且,地理學家早已認定,今日地球上草原生態的雛形,在七百萬年前就已奠定了基本輪廓。人類憑一己之意的強迫,挪闢,不過是短暫徒勞的弱力。大型推土機猶如此,何堪人力。
當我試圖拔除那扎根在樟樹底部的大株姑婆芋時,樟樹的根也被我鏟斷了。同樣的困頓也發生在菜園裡,纏繞住南瓜根莖的野莧與地瓜葉。
野莧與地瓜葉就不好嗎?人類所判定的雜草,未必如表面所見顯得客觀,先驗,決絕。雜草,不單涉及可食或不可食這看似生理性的前提,彷彿是被動的,先天的拉力。或許,更多是一種推力。以分類學來看,何謂雜草,是奠基在「人類獨特主義」下的產物,包括世界觀的建構,認識論的補充,分類秩序的維護,一連串有意識的囊括或剔除──環繞著以「人」為中心的敘述,久久糾纏並根植在人類的基因,情感,記憶。
作為獨立的個體,我擁有判斷的無限自由這我知道,但作為純園的勞動者之一,我仍必須把瘋長的姑婆芋鋤去,因為這是一塊為了原生樹種包括烏心石、毛柿、樟樹所建立的園區。在有限的地理疆域內,它的理想是值得服膺的,我願為之刀耕,躬身,跪地,以手掌整平土壤,撿拾殘留的根莖。
無限的自由只使人備感漂移和虛無;而現實的有限則能貼地,使得關懷有了著陸和起飛的跑道。以地球為尺碼的理想縱然遼敻,不免也邈在鄂渚,鞭長莫及。若改以自己的家鄉,以島嶼的尺碼來度量腳下的土地,則脈絡相連,可以應援。一個人的情思主體,若要能寵辱不驚,開放而有情,或也能引此為戒。
◇日落
溪州的日落比任何地方都漫長,趁著風涼而一時日照未歇,我抱起二十幾根黑泥季的旗幟走向田區。有時,我們也在這裡用竹竿挑起濕潤的稻草,翻面燃燒,或者一起坐看收稻機滾過田野。
旗子太重了,雙手協力也只能勉強撐住,腳步遂在田埂上搖搖晃晃,一邊是即將收成的飽穗,一邊是泥漿化的田水,兩邊不能踏空,恍如走著鋼索。
抬頭,陽清為天;垂首,陰濁為地。極目遠望,這是濁水溪開天闢地的沖積平原。其水之永,不可方思,只能遙想在中央山脈與雪山山脈之界,好幾條不可預知,或許就是上古時期早已存在的清澈水源奔流而至,急湍相會,又聚合歡以西的側水,奮力下切,衝撞為上游處閉塞的曲流,仍持續漫漶,濡染過山脈背斜之上,那些發達的第三紀粘板岩,不畏崎嶇,斷層,與崩塌,無所謂挾帶一身混濁的沙屑,終以泥漿之姿開創一條路徑,如瀑布切割,在八卦台地和斗六丘陵的山脊間大開,湍流東擴,海拔高度陡頓突降三千米,並攜以年均輸沙量六千三百萬公噸的泥沙礦物,鋪排盈盈黑土至今不停,由上而下展開河階,河谷,沖積扇與無數支流,其中之一就是莿仔埤圳,灌溉著眼前這面溶溶反光的水稻之鏡,最後平靜長注于台灣海峽,托著波濤上那顆落日在浮沉,而一群黃頭鷺將振翅飛往,牠們澄亮的簑羽因夕照而更顯金黃。
現在,一天的工作已結束,我可以舒一口氣,並將菸蒂收進口袋裡,走回小屋,洗把臉更衣,趕赴三合院,吳晟老師一家人已替我們這些小孩備好酒飯。
◇人定
最先迎接我們的總是黑米。是吳志寧救回了牠,幼年流浪時因塑膠套住頭部而腦缺氧,成年後神經兮兮,見人就吠,動輒要咬。即便如此牠仍備受吳家疼愛,我看得出。當黑米失控,客人慌忙走避時,吳志寧總能迅即安慰牠,所做的不過是蹲下,捧起黑米的頭,眼對著眼,溫柔地撫觸。
桌椅排開小院落,吳晟老師與我們在樹下吃著家常的大碗麵,聊文學,喝啤酒。經幾日勞動,再要討論生活與詩時,我們竟直接援引土地做為隱喻而不自覺。有人說土地讓他重新思索,愛,無非就是予對象以空間,讓萬物自然生長;有人發現,無論從什麼方向回純園,只要沿著水圳一直走,就能回家,這令他無比感動;還有人說,大多數人並不知草木的名諱,遑論它的生長特性,或許對現實世界的一知半解,同時也造就了對文學創作的一知半解。
吳老師耐心聽著我們對土地自然的感悟,默然點頭,靜靜思索,每次都能娓娓舉出實例來呼應,引發對話與想像。譬如七里香,吳老師說,又稱月橘,本來並非一種圍籬植物,卻被人廣泛地移植,屈就,修剪得方正齊整,只為悅目。若給予它充分的自由,便能發揮天賜的異稟,其花葉,樹皮,樹脂,木材都有妙用。但當平靜而深刻的話題轉向十年前的護水運動時,吳老師也有悲憤難遣的時刻,調息幾分鐘,還要接著聊下去──如溪河緜緜的話語,這樣灌溉著我們,直到宴散,放下飲盡的殘杯,我知道吳老師又將轉回書房,埋首於層層堆疊的筆記庫,檔案夾,簡報本,在夜半的窗下趕稿。
而我將追著涼風,踏著月光回到純園,發覺自己再不感到那凡誕生於世所皆有的流亡,焦慮。曾經,我鎮日戮力維持著精神的敏感與尖銳,等待電流般的通感或療癒,期待這世界賦予我的靈魂以意義,心思但凡搖動,起了微妙的變化,便會樂不可支,這些都是為了什麼?為了一首不存在的詩。事實是,這世界不曾賦予我的靈魂以意義,而那首詩或將永遠不會存在,但是這又如何。當我從樹林深處抬頭,看見一對螢火蟲在明滅中試探著彼此,縱然一生一次,縱然以覆滅為代價,我知道,信任與愛仍是可以言說的,而人生並不一定為那首詩而活,甚至並不一定為了自己的靈魂而活。儘管這是極度不安的,儘管這就是生命的開始。
❝ 用一生的汗水,灌溉她的夢──吳晟〈泥土〉❞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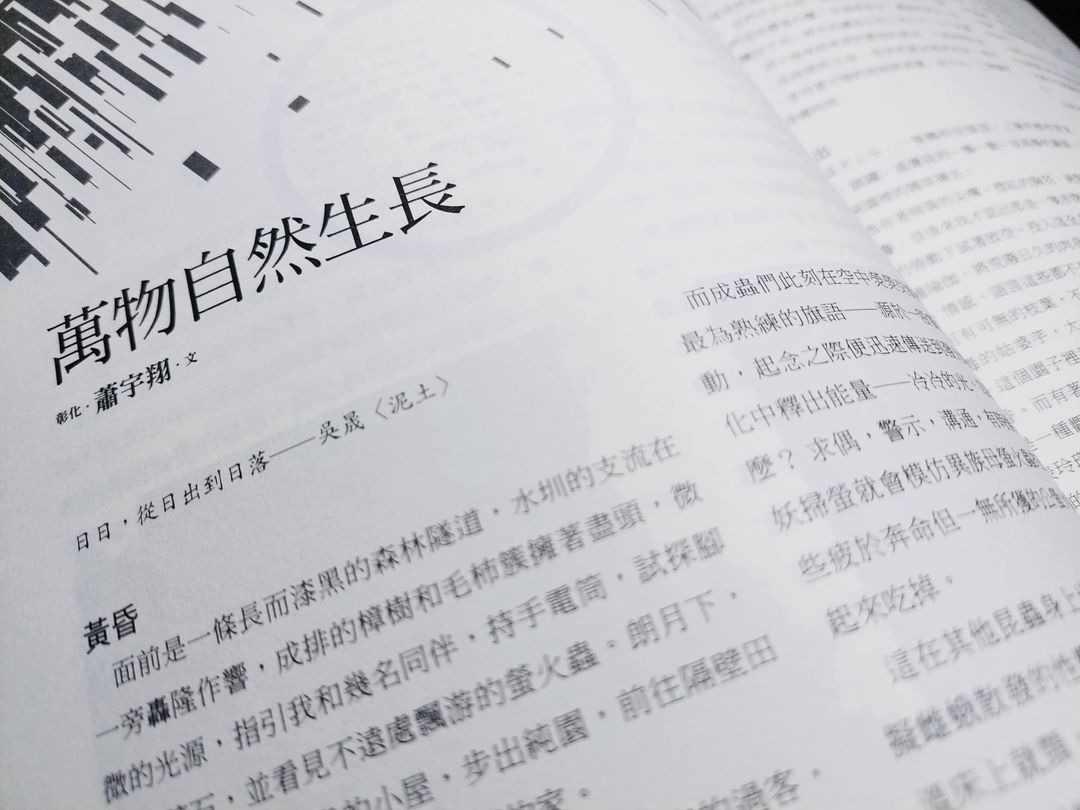
{{ $t('FEZ003') }}2022-11-28
{{ $t('FEZ004') }}2023-04-17|
{{ $t('FEZ005') }}343|
